广州大城市的文化资源果然丰富多彩。大概几周前,粤博的公众号就发布了《秘密道具博物馆》口述观影的活动预告,楼主在看到的第一瞬间就预约报名了。实地参加完这场观影会,我感受到这是一次充满人文关怀的观影盛宴!

观影会的核心是“口述观影”。毋庸讳言,楼主对这一概念是陌生的,参加活动的初衷也是希望观赏《哆啦A梦》而不是这个特别的形式。但到现场实际了解“口述观影”的概念后,我才知道这是一项旨在服务视障群体的特别观影服务。简言之,就是在电影对白的空窗期插入口述员的旁白,把电影情节穿插成一个整体,使视障群体也能相对完整的享受电影内容。主办方为了让健视观众更好体验口述观影的作用,在正片之前还放了《小丑鱼》片段三遍——第一遍为纯音频、第二遍为音频加口述,第三遍为音频、视频和口述的结合。这种方式应该会使健视观众递进式地了解口述观影的作用。但是,这个片段的口述员在口述时使用了粤语。对于完全不懂粤语的楼主来说,音频加口述的第二遍反而是最费解的一遍。
了解了活动的初衷和主旨,楼主替主办方捏了一把汗。《秘密道具博物馆》这部作品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私以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原创剧场版),它是把未来作为舞台,以破案为主题,涉及到大量奇思妙想的道具和时空穿梭情节。虽然电影的叙事结构不能说是最复杂的,但也有一定的“烧脑”程度了。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口述观影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或许是因为观影会在粤博举办,才选了和举办地关联密切的《博物馆》也说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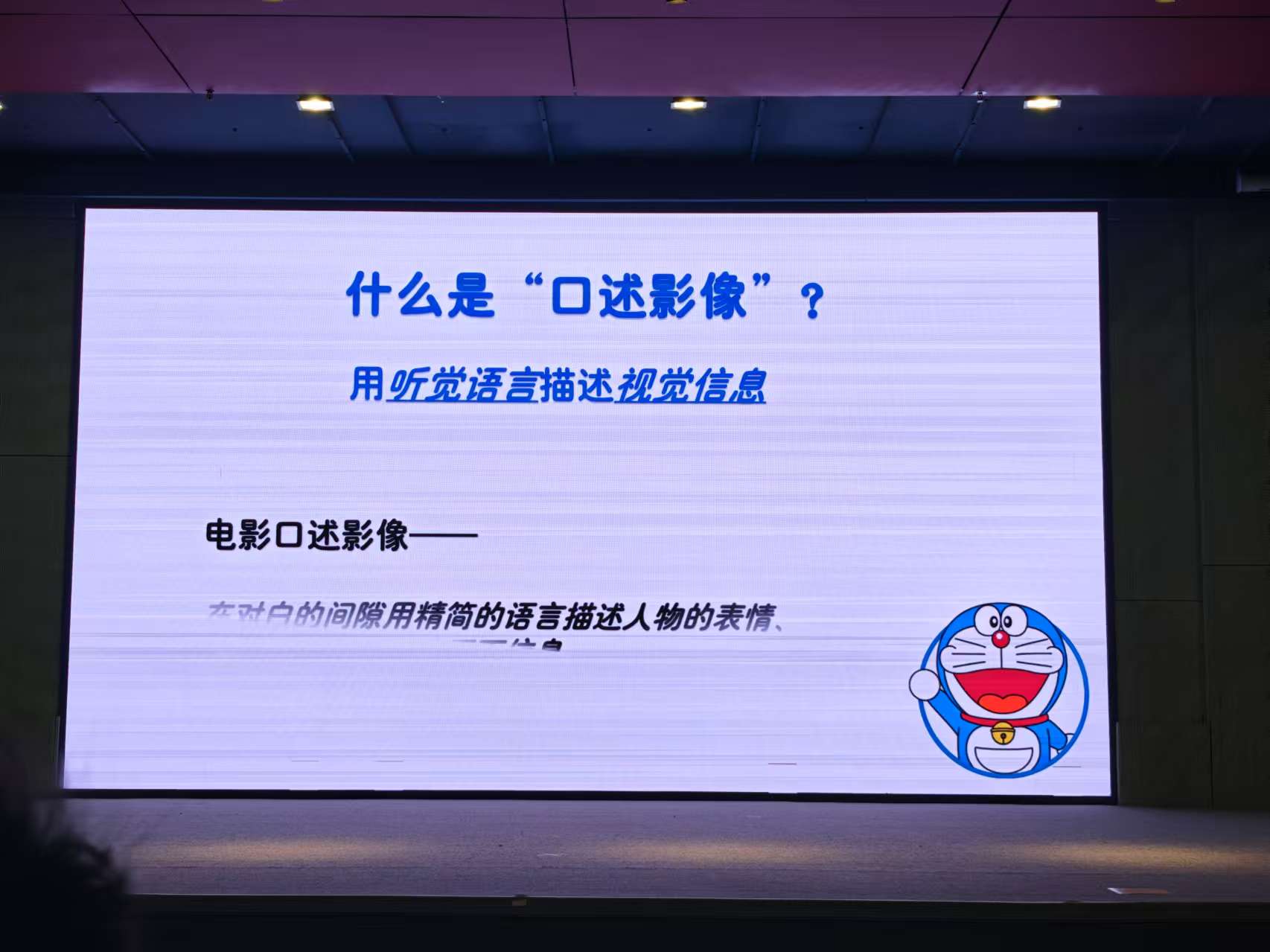
作为老牌哆啦迷,《博物馆》的情节楼主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因此在电影一开始,楼主打算模拟视障群体,闭上双眼,用想象力去拼凑台词和口述旁白。虽然实际只坚持了半小时左右(在有声、光的刺激下一直保持闭眼是很累的事,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但也让楼主感受到口述观影方法的魅力。和楼主预想的不同,口述旁白并不是对电影事无巨细的解读。它把自己的功能严格限制在了台词的间隙,更注重加强台词和台词之间的衔接。对于转场,口述旁白一般不加描述(对于视障群体来说,或许可以凭借更敏锐的听力从背景音乐的变化感受电影的转场?)。而对于内容,口述旁白也不得不加以取舍。例如,当库尔特带领大雄、哆啦一行人步入博物馆时,楼主的注意力完全在巨大的初号任意门上。当我以为旁白要描述初号任意门的宏伟时,口述员却把重点放到了哈特曼博士的雕塑上。结合下一个分镜,这种取舍的用意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库尔特要向大雄、哆啦介绍哈特曼博士,而视障群体是不能感受到哈特曼博士雕像的存在的(健视观众虽然也可能在上一个分镜中忽略雕像,但在库尔特介绍时就很轻易的感受到了),必须向他们交代雕像的存在,才不至于使他们跟丢剧情。
楼主的另一个误区是:口述观影不是看图说话,他必须用有限的时间快速描述剧情。因此有时候会出现短暂的音画不同步。例如大雄、哆啦一起找铃铛的情节,旁白对情节的描述是要略快于实际剧情的。这是因为口述观影立足于服务视障群体,不必背上必须音画一致的包袱。对于大部分情节来说,旁白的语速都是比较平和的,但当剧情快速发展而台词间隙又比较小的时候,旁白也不得不以极快的语速来跟上电影。例如,在“大雄钓机器甲鱼”这个情节中,旁白要交代清楚
①大雄玩钓鱼游戏,钓上了机器甲鱼
②甲鱼钻进了哆啦的口袋,导致道具无法拿出
③甲鱼长期留在口袋,矛盾并未解除等信息。信息密度很大,使得旁白语速也变得飞快。
楼主感受到,口述旁白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口述员对于电影想传达给观众的信息,必须做出取舍。一些细节——哪怕非常有趣(例如哆啦A梦“铃铛”的变化)——因为去掉不影响主线均被统统舍弃。例如,对于人物的外貌,旁白几乎没有描述。关于胖虎、小夫独立侦查,怀疑馆长的细节,也没有被描述。另一方面,口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库尔特的萌宠“碰碰”,大家知道它是飞在空中的。但结合口述和台词,观众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只在地上跑的动物。
和影评、译制等工作一样,口述大概也体现着口述员对电影内容和情感的理解。比较表层的一点就是语调和语气。大部分时间的口述都是比较平缓的,但当大雄、哆啦、库尔特等人力战太阳的时候,口述员的语气也变得紧张和激昂起来。这使得健视观众的紧张感也加剧了。
影片结束后还有问答和文物解说两个环节。问答是针对小孩子的(来观影的不仅有视障人士,还有一部分冲着看动画片来的小孩和家长),就是一些简单的电影情节。文物解说是由粤博馆员为视障人士解说馆藏文物。被解说的三件文物有恐龙骨架模型、罗马人像模型和商周青铜器。解说让人感到视障人士了解世界的不易。尽管馆员去竭力描述剑龙模型,但一位视障大爷还是错误地理解了它的大小、体型和习性。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活动确确实实让人感受到了包容和人文关怀的氛围。主办方对视障群体和健视群体、大人和小孩都有兼顾。顺带一提,隔壁的广州图书馆(本帖就是在这码出来的)一楼就是视障人士阅览区,能够体会到大城市的先进和开放。(当然,也能体会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最后探讨一个电影本身的点(楼主虽然看了多遍,但这个视角是首次发现,所以记在这里)。电影中,发明了全金属的哈特曼博士可以说是秘密道具之父,而他的孙子库尔特则是难以望其祖父项背的新手道具师。库尔特一心想要制造出超越前辈,足以被博物馆珍藏的新奇道具,但却屡屡失败,直到影片最后也还在探索阶段。但回到现实,凭着天才般想象力创造那些秘密道具的,不正是藤子·F·不二雄老师吗?承载着全部秘密道具的博物馆,不正是充满梦想的《哆啦A梦》世界吗?而库尔特这个后辈,又何尝不是在藤子老师逝世后,试图循着他的脚步把《哆啦A梦》世界延续下去的创作团队的写照呢?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库尔特的独白简直就是电影制作组在超越时空和藤子老师对话:“老师,我们创作的道具,合格了吗?”尽管“库尔特”没有“哈特曼”那样的才华,但他对“秘密道具”的爱是无可否认的。不言而喻,如果《哆啦A梦》由像寺本幸代那样热爱它的人来创作,那么即使达不到大师的高度,也未尝不会出现亮眼的火花。反之,要是缺乏了对作品最基本的爱,那么衰败也并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