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吧刊文化是中国粉丝以业余文化生产的方式,把自身所在线上社区的文化与内容作粉丝再现(如同人小说或业余漫画的形式)。笔者以“机器猫百度贴吧”生产的电子爱好者杂志《猫吧吧刊》为例,展示线上粉丝社区的参与式文化、业余文化出版及中国青少年的粉丝文化。笔者认为,新世代的中国青少年粉丝(90后及千禧代)掌握了一定的科技与媒介素养,能以媒介融合的方式,把喜爱的媒介客体转化成偏好的表现形式,从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成参与者。
关键词
吧刊文化、青少年粉丝、参与式文化、业余文化生产、百度贴吧
简介
在中国内地,学界对青少年粉丝(Young fans)的研究始于千禧年末,蔡骐等以媒介心理学的方法作研究,认为“粉丝”身份较之于普通受众有着行为和心理上的差异,“追星”是青少年心理矛盾运动的产物, 不仅有其过渡性和合理性的一面,也有着令人担忧的一面。[1]殷乐认为,“如何彰显并引导青少年娱乐消费,形成与迷文化之间的建设性关系,并减弱其因过度而导致的负面影响,有待媒体、家庭、学校和青少年自身的多重合力”。[2]谢琰认为:“青少年粉丝文化的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多种社会负面效应,首先,社会大众应予以高度重视,而作为具有影响与引导青少年粉丝文化功能的各级社会单位也应采取积极措施。”[3]这些研究倾向聚焦青少年粉丝作为消费者的角色,较少关注其作为积极参与者(active participants)的角色,而后者着力于对他们喜爱的粉丝圈客体进行创作与保存。
欧美的粉丝研究倾向把粉丝视为积极参与者,詹金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著作《文本盗猎者》提出“参与式文化”的概念——“]粉丝圈在这里成了一种参与式文化,将媒介消费变成了新文本的生产,或者毋宁说是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4] 彼时他把参与式文化等同于粉丝圈(fandom),未对其进行理论化。其后,他在著作《融合文化》中,把参与式文化定义为“邀请粉丝和其他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新内容的创作和传播中来的文化”。[5]参与式文化与粉丝圈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延伸至数字媒介——在艺术、文化、政治、教育及宗教领域上展开广泛讨论。[6]
在中文学术界,孙绍谊于2008年在《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介绍了詹金斯“参与式文化”的概念、“兼具粉丝身份的学者”的研究立场;杨玲梳理了“参与式文化”在国内的研究路径,例如,纪莉[7]、吴世文[8]、郜书锴[9]对詹金斯“融合文化”理论的借用,以及詹金斯在自身研究上的变化:他“放弃了‘文化融合‘’这个术语,不再试图建构一个媒介融合/文化融合的二元对立,而是用一个更包容性的‘参与式文化’概念来描述受众的媒介活动。”[10]汪金汉综述了詹金斯在《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世纪的媒介教育》提出的参与式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内容[11]。
然而,关于参与式文化,中文学术界较少对本地的青少年粉丝作实证研究。本文着力于此,力图解答的一个研究问题是:中国青少年粉丝发展出怎样的参与式文化?本文将从参与式文化、业余文化生产、数据库消费等三个层面对此问题作阐释;本文研究的青少年粉丝以90后和千禧代为主,他们属于数字原驻民-——自小“泡”在网络世界、具有一定的科技和媒介素养。
参与式文化
詹金斯认为,“媒介消费的模式因一系列新媒介技术而遭到了深刻的改变……参与式文化指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浮现的消费主义的新样式”,这种文化的背后,实际是“媒介消费者想成为媒介生产者,而媒介生产者则想保持它们对媒介内容的传统主宰”。[16]百度贴吧自2003年成立至今,已拥有15年的历史,中国粉丝已逐渐与媒介生产者建立起“共生”的关系。以《猫吧》为例,经过长期的实践,他们与媒介内容的中国代理达成了共识:在《猫吧吧规总则》中制定删帖规则:“关于艾影(上海)即大陆官方在大陆地区举行的活动,本吧吧务会删除未经授权的盗版《哆啦A梦》活动的帖子。”[17] 这里提及的“活动”主要是线下活动,如海南省某地产商曾举办了未经授权的“哆啦A‘萌’人物展览”活动[18],一旦粉丝在《贴吧》发布,信息随即会被“吧务”成员(由44名核心粉丝所组成)删除。然而,粉丝作为媒介消费者,他们生产的媒介内容还会受到网络公司的制约,笔者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中国,参与式文化始于80年代中期,彼时内地居民已拥有600多万台录像机[19],到了90年代初,录像机已相当普及[20],粉丝可收藏大量的媒介内容;粉丝重新剪辑电视节目的内容则始于千禧年中期,网络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诞生,“开始重塑互联网景观的生态“[21]。2003年11月,百度贴吧成立,粉丝在此为自己喜爱的媒介客体建立子贴吧,而“吧刊文化”则始于2007年初,核心粉丝按照百度公司的要求成为了“吧务”,他们以“官方粉丝社区”的名义生产和发布数字爱好者杂志。起初,所在粉丝社区的成员会把自身撰写的粉丝文本投稿给负责“出版”的核心粉丝,再由核心粉丝整理后,以文字为本的模式(text-based modes)发布。到2007年10月,粉丝已能透过Photoshop 拼贴技术创作任何视觉形式的影像,《猫吧吧刊》首次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信息(图1.1)。正如詹金斯所说:“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还帮助打破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互联网使得各种另类的媒介生产获得了更高的可见度(visibility),并超越局部公众(localized publics),进入更大的传播范围。”[22]

事实上,粉丝生产的粉丝文本并不限于自身喜爱的媒介客体及所在的虚构世界,他们生产的媒介内容还包括知识和个人经验的分享,《吧刊》由此成为了粉丝联系现实世界的信息交换工具。例如,2013年4月,四川发生了芦山地震,粉丝在以民族主义的话语(nationalist discourse)在《吧刊》表达群体的想法:“上次汶川地震,我们感受到了国人的团结,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决不放弃’……地震,它能让中华儿女团结起来!”[23],他们甚至挪用虚构角色作“爱心大使”,籍此为受灾地区的人民打气(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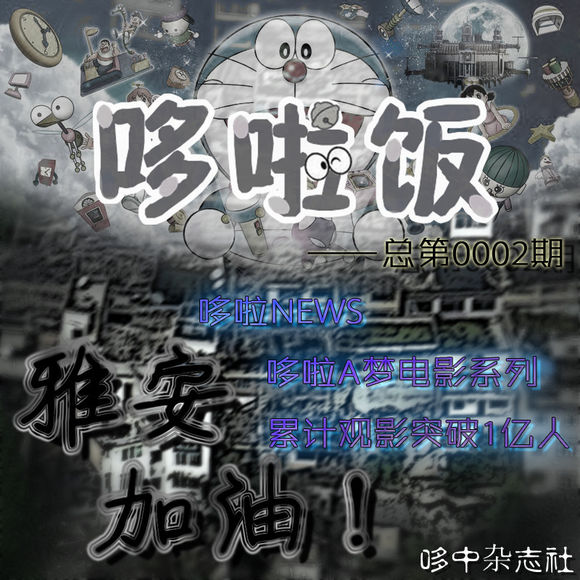
数字爱好者杂志属于“地下文化”(underground culture):“这种文化……是在较大型的异化社会中生产,在替代文化和主流社会之间,界线持续被绘制: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正直与出卖,纯洁与危险……地下文化的根源在于它与主流社会的分离——它顶点的存在源于这种否定。”[24] 在商业社会,新媒介公司机器扮演着主导媒介的角色,它们试图监管粉丝生产(fan production),例如,百度公司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推出的“吧刊平台”,原意是令“编辑功能更强大,发布更系统,浏览更便捷”。[25]这个系统需要由所在贴吧的核心粉丝——吧主负责申请,并授权给委任者使用,目的是让粉丝监管自身发布的信息内容。然而,粉丝并没有严格执行:他们只使用平台的图片上载功能,没有把图片和文字分开处理。由于平台无法起到监管粉丝发布内容的作用,百度公司以 “吧刊的制作、浏览人数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也为了将更多资源用于发展贴吧的新玩法”[26]为由,将“吧刊平台”关闭,部分核心粉丝作为文化干扰者(culture jammers),在他们所在的子贴吧或社会化问答网站知乎上批评公司机器(corporate apparatus):“吧刊作为一个社区共同的文化作品,对整个社区还是很有意义的。水准低、浏览人数少,固然和制作者、贴吧运营者有关系,但也说明了百度在吧刊这个功能上做得不够好,不吸引人参与、不能方便大家制作好的东西,传播性也差。但毕竟来说,对百度公司不那么重要,对大部分贴吧用户都不怎么重要的吧刊,曾是贴吧的核心用户努力的心血,百度公司以粗暴简单的方式应对:在某些官方贴吧发个公告,然后就下线了。一个产品能不能有始有终?你既然没能力,将贴吧升级或转化成更活跃更好的产品,那么用心点,也给大家提供一个‘一键备份’的工具吧?”(知乎匿名用户,2016年7月27日)[27]
尽管粉丝拒绝认同公司机器的行动,然而,他们并未以“粉丝行动主义” (fan activism)作草根表达。所谓“粉丝行动主义”指涉的是“粉丝文化本身浮现的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形式,经常通过现有的粉丝实践和关系,以及通常从通俗文化和参与式文化中提取隐喻进行构建”[28],例如,以“迷因”(meme)的形式作表达——“透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一个滑稽或有趣的项目(例如带字幕的图片或视频)或项目类型” [29]。如图1.3中,美国粉丝挪用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主角与美国现任总统握手,表达他们的某些政治或文化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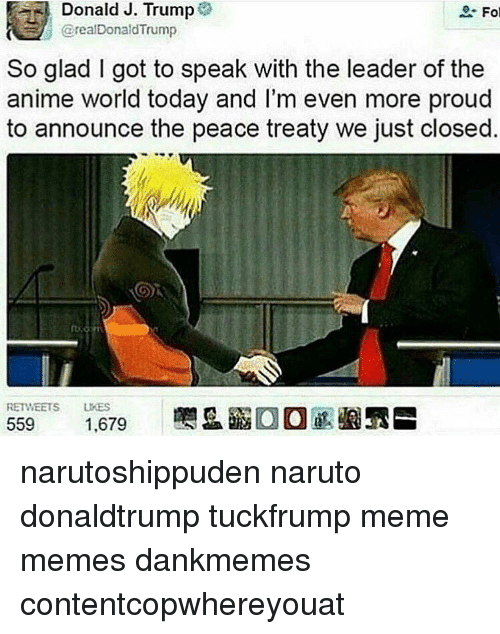
然而在中国,基于外在的环境原因,很少出现激烈的粉丝行动主义。在百度贴吧,尤其是日本动漫粉丝,会刻意把媒介内容区分为“二次元”与“三次元”,前者指涉的是以日本动漫为本的虚构世界,后者则是现实世界。这种区分的目的是,粉丝圈不希望粉丝于所在的子贴吧讨论政治事宜,例如,在《机器猫吧规规则》中,有相当清晰的条文:“政治相关帖子删除概率大,如果引起争吵或者有违法律,删(除)。”[31] 在“百度公司关闭吧刊平台”事件上,参与吧刊创作的“编辑部”成员,同时兼任“吧务小组”的删帖工作,他们若是在所在子贴吧号召任何的粉丝行动,会同时冲击自身所守护的《吧规》,因此,他们选择以集体分工的形式,对媒介内容进行存档,再上载到特定用途的网络公地(the web-commons)——“粉丝利用网络社区、社交,以及万维网的传播属性,形成的依赖友情和分享的社交群体”[32],使所在贴吧的粉丝可再次阅读吧刊。
吧刊与业余文化生产
如上所述,在机器猫百度贴吧,青少年粉丝倾向不作政治的隐喻表达,而是以新故事展现与原作文本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视这些文本为创作或解释的基础”。 [33] 他们视自己为参与者,所建立的粉丝文化“因而代表着一种参与式文化,透过这种参与式文化,粉丝从一个时而内在于、时而外在于商业娱乐的文化逻辑的立场,探索和质疑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34]以媒介客体《哆啦A梦》为例,其商业娱乐文化逻辑是“哆啦A梦是没有结局的……会继续下去”。[35] 对《猫吧》的粉丝而言,“有无结局”成为了一种“道德二元”(moral dualism),即“好”粉丝和“坏”粉丝,[36]分别被粉丝圈冠以“主流”和“非主流无意义”粉丝的称号。“主流”粉丝希望为原作文本留下幻想场景(fantasy scenarios),意思是并不会得出最终版本的结局,而是利用同人小说“将影视内容带入到一些不太可能获得广泛传播的幻想,并通过重新剪裁加工来适应文化缝隙群体的需要”。[37]例如,粉丝安排其中一位主角(哆啦A梦)在剧情中死去 ,直接控制媒介生产者的“知识产权”:“为了达到相应的剧情效果,我在同人故事中,让主角之一的哆啦A梦在故事中死去,这作为铺垫,目的是让另一个男主角大雄的心灵成长剧情得以展开,上述的剧情效果和结局是预先定好的。接着,我开始收集素材,然后进行重写,过程中,‘编辑部’的成员会给我一些建议,但不会详细讨论文章的情况,因为我的创作是相对独立的。”(哆啦编辑部成员“沉沦的默默猫 ”,2018)
除此之外,粉丝把“参与式文化”的权利,当作是一种“自由”,他们把原本受媒介生产者或公司控制的“知识产权”理解为“共享软件”、詹金斯把粉丝的这种理解作如下诠释:“只有靠不同语境的移动、不同方式的重述、对多样受众的吸引,以及另类意义的扩散才能累计价值”[38]。在“编辑部”,中国的青少年粉丝亦给与笔者相似的反馈,个体粉丝把自身的幻想逻辑以草图的形式作表达,而具漫画素养的粉丝则将这种幻想逻辑作视觉再现(visual representation):“此次漫画的剧本,是我在一瞬的灵感中确定的,在此之前,我的目标是‘喜剧、轻松、简洁’,这是由吧刊的性质来确定的,总的来说,还是在很自由的创作环境下,加上粉丝‘万物神尊’的超强绘画能力,让我有了足够创作自由,很享受创作带来的乐趣。先是灵光一闪,然后,是一点一点捋出下一刻、下一秒的故事,当故事的前奏确定了,下面的故事就如文字游戏一样,会顺理成章地发展。”(编辑部主编傅皓衍 ,2017)
《哆啦A梦》粉丝圈、数据库消费及青少年粉丝
《哆啦A梦》的漫画诞生于1969年,原作者亲自绘画的故事有1345回,它的电视动画于1973年起于日本播放至今,而中国的青少年粉丝主要透过视频网站观看,系列电影亦于中国内地上映。《哆啦A梦》的故事模式是:“哆啦A梦因应大雄的要求,又或是他自己的判断,轻易拿出适合解决当时情况的荒诞道具。然后,那道具引起周围人荒诞的反应,带来荒诞的结局。”[39]Allison 把这种故事模式归纳成《哆啦A梦》的幻想逻辑:“故事情节是以普通孩子为中心前提,这些儿童既能‘利用高科技机器挖掘连接异世界的有趣东西,又能获得帮助主人实现幻想的伙伴,二人的羁绊(bond)是一种服务和友谊的混合,这些幻想生物是甜蜜且实用的,情节的驱动是通过把幻想来源的权力转移和转化给人类的孩子。” [40]
中国的《哆啦A梦》粉丝圈的阅读兴趣是两位主角之间的羁绊,他们不断想看到发生在喜爱角色之间的剧情,东浩纪把这种粉丝现象称为“过视的”(hyper-visual),即“永不停止尝试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的这种泥沼状态”[41],因此,他认为,日本御宅族的信息消费过程是透过双层结构来实现的,这种双层结构分别为:1)数据库包括了非常零碎的非叙事萌要素(non-narrative moe elements);2)小叙事——讲故事所使用的角色是从数据库中提取。[42]上述提及的“萌元素”指涉的是特定角色的性格,包括:人物衣着、言谈的语气、个性,甚至与主角的关系。日本动漫产业会按照读者的类型,把漫画分类为儿童、少年、少女、成年漫画;另外,媒介集团还设有读者反馈机制,经过长期以来的实践,他们总结出自己的编辑政策,例如,包括 “友情”、“毅力”、“胜利”等要素的日本漫画一般均能成为当地的畅销书[43]。日本的媒介生产者通常实行“跨媒介制作”(media mix),它描述的是,以角色为基础,链接到游戏、动画、漫画,在作品中加入上述要素,以保证收视或票房。
粉丝消费喜爱的媒介作品,他们把自身的“过视”归纳为喜爱人物的“价值观”,甚至不吝与其他动漫人物进行比较,籍此证明自己对人物的偏爱是“合理”的:“在系列电影中,大雄的表现非常耀眼,光芒甚至盖过其他角色,这一点在电视动画的‘剧场版’系列更为明显。最后一点,有别于那些把‘平凡’挂在嘴边,实则非常厉害的轻小说主角,我觉得,大雄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普通人,他有我们身上的优点和缺点,读者很易从大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许多同人作者会下意识地把自己代入大雄,成为自己所撰写故事的主角。”(同人作者王多啦君 ,2016)
在《猫吧吧刊》中,两位粉丝共同创作的业余漫画《消失的铃铛》就是一例,青少年粉丝把角色之间共同经历的剧情视为对个人生活来说“情感上”的事实,洪美恩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情感现实主义”(emotional realism):“实在的情景和复杂纠结的矛盾被视作对更加普遍的生活境遇的象征性表现:争吵、秘密、问题、欢乐和忧愁。”[44] 詹金斯则把“情感现实主义”视为“并非虚构故事本身的属性,而是一种粉丝阐释虚构故事、赋予流行叙事意义而构建出的他们眼中的虚构故事。”[45]青少年粉丝参与同人故事创作时,倾向提升角色的情感强度(emotional intensity),例如,在图1.4的业余漫画《消失的铃铛》中,粉丝为角色加入视觉或语言的数据库“萌要素”,如心理状态、情绪状态、语言等等,使原本常常表现出“男子气概”的哆啦A梦变得情绪化,而原本“情绪化”的大雄拥有“男子气概”;与此同时,让他们喜爱的角色不断经历“小叙事”,故事得以“永远”处于粉丝偏爱的“过视的”状态。

在同人作品中,粉丝保留了原作的“大叙事”,包括“设定和世界观”。[46] 例如,粉丝沿用了原作的设定——“现代世界”故事场景,至于“世界观”则是同情(empathy)。彼得(J. M. Peters)认为:原作者藤子·F.不二雄的漫画如此流行是因为他能真实感受到大雄和日本儿童的强烈同感。[47]德拉赞(P. Drazen)将《哆啦A梦》的“世界观”解读为“佛教的基调”,即“同情所有众生”。[48]对粉丝而言,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漫画视为一种将喜爱的虚构角色带到“现实世界”的方法:“我很希望‘哆啦A梦’能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希望我的《哆啦A梦》同人故事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贴近,也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其中源于生活的乐趣。我希望这件事可以传递到生活,在快乐的时候,想到哆啦A梦,或看到他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快乐,这都是我想要的。(编辑部主编傅皓衍 ,2018)粉丝的这种想法实际就是让·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提出的概念“超真实”(hyper-reality)——“我们在生活中主要不是使用者,而是阅读者和选择者,是阅读元件。”[49]他的意思是现代世界的“真实”是由符号(电脑或电视的视觉影像)建构出来的,其将原有的真实取代并超越之,从而深刻影响了观者自身。
总结
日本的动漫文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进入中国,由于当地动漫产业的长期实践与经验的累积,立即吸引了部分80后世代的中国青少年,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的青少年动漫粉丝,然而,由于当年的科技发展及教育水平所限,中国青少年仅能以消费的方式观看或购买动漫产品。互联网的普及化,使新世代(90后、千禧代)的中国青少年可以随时在网络学习不同的媒介和科技素养,尤其是线上粉丝社区百度贴吧的出现,让他们有机会认识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相互学习,共同为自身偏爱的媒介客体创作新的内容,发展参与式文化。在本研究中,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能很好地阐释中国青少年的线上文化参与现象,例如,粉丝把媒介生产者的“知识产权”视为“共享软件”,把自身对媒介客体的幻想转化成多元的表现形式,同时,青少年粉丝自行制定和遵守网络参与的守则,以理性的方式作线上参与。粉丝的业余文化生产,在视觉上,以“超真实”的方式,把自身喜爱的角色和“世界观”带到“现实世界”。中国青少年不断把自身的幻想转化成创意,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成长。
研究方法
笔者从事研究时,将自身的身份认同视为“粉丝-学者”(fan-scholar),这是学者从事粉丝研究的一种立场,即研究者既是粉丝,也是学者。粉丝(fans)本身是一个身份,“作为媒介客体(media object)的一部分”,且把自身与其他的媒介阅听人区分开来[1];成为粉丝(being fans)则意味着认同媒介文本。而作为学者对粉丝进行研究,则允许研究者“探索一些我们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现实和身份认同的关键机制”。[2]“粉丝-学者”一词是由马特·希尔斯在他的2002年专著《粉丝文化》中创造的,被定义为在面向粉丝圈的作品中使用学术方法和理论的粉丝。[3]
笔者是日本动漫《哆啦A梦》的粉丝,自8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收看该节目、购买及收藏其相关的玩具、漫画、影碟。鉴于笔者对“粉丝-学者”的身份认同,从事本研究时,选择进入线上粉丝社区“机器猫百度贴吧”(下称“猫吧”)。它与线上论坛百度贴吧同步创立于2003年11月,从2003年11月至2018年3月,已存储超过900万条的帖文(2018年3月4日的帖子数目为9,008,503条,为粉丝发帖及留言的总数),并发展出独特的“吧刊文化”,体现在粉丝以免费劳动力共同制作的数字爱好者杂志(digital fanzine)上。以《猫吧》粉丝创作的数字爱好者杂志《猫吧吧刊》为例,从2007年至2016年,共发布了45期(详见“参与式文化”部分)。本文填补了粉丝研究的一个空白,内地学术界尚未见到对“吧刊文化”这一粉丝现象作研究。
研究开展于2015年8月至2018年3月,分别在线上论坛机器猫百度贴吧》、即时聊天群组《编辑部》腾讯QQ群、社会化问答网站《知乎》上进行线上民族志的田野工作(online ethnographic fieldwork),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4]2015年8月,透过百度贴吧创建个人账号后,笔者定期于此发帖,共发布了54篇介绍《哆啦A梦》玩具的帖文,随后,每次进入社区均会点击“签到”按钮,提升自己的贴吧等级(笔者现时为9级,某些粉丝活动需要8级或以上才能报名参与,例如“猫吧杯知识竞赛”);在此过程中认识核心粉丝,平日与之进行线上互动,透过贴吧的私信功能邀请他们接受深入访谈。2015年11月,笔者希望观察《编辑部》生产《吧刊》的模式,因此,应“主编”的要求,撰写过一篇围绕《哆啦A梦》的同人小说,籍此成为了“编辑部”的成员,亦向成员告知自己此举的目的,并没有引起诸如伦理纷争的问题。
笔者收集的资料包括:1)2007年7月至2016年6月共45期的《猫吧吧刊》;2)深访了23名核心粉丝,年龄介乎15到33岁,时间介乎1.5至2小时,部分核心粉丝至今依然接受访问,共录得6.6万字的田野笔记;3)粉丝把部分的信息发布于《知乎》,因此,笔者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阅读相关的帖文。
镇图的同人作者:
多谢以下各位猫吧大佬奉献宝贵的时间,排名不分先后:
- 邻家的王子
- AS大雄
- 悟空№哆啦
- 王多啦君
- 万物神尊
- 哦几公分发如风
- 丶瘋癲男仔
- 点爆星蓝
- 我永远爱丝丝
- 世界——地图
- 虫虫A梦
- stf1
- 小于妹子
- 雷龙B
- 晓月冷寂
- 傅皓衍
- aidlam
- 沉沦的默默猫
- 鸟山千雄
- 蓝粉团多啦神圣
- 岚天X
备注:特别特别特别鸣谢:
无论上学、生病、各种玩之下,都乐意回答我任何问题,感激~
参考文献
- ^ SANDVOSS C.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M]. Cambridge: Polity,2005:101.
- ^ GRAY J, SANDVOSS C, HARRINGTON C L. Introduction: Why Study Fans? [M]. // GRAY J, SANDVOSS C, HARRINGTON C L.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 ^ HILLS M. Fan Cultures[M]. London: Routledge, 2002: xvii.
- ^ ARDEVOL E, GOME-CRUZ. E. Digital Ethnography and Media Practices. [M]. VALDIVIA A 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2013:1.